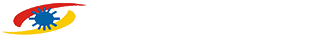勒内·马格利特
- 时间:2017-04-15 11:04
- 来源:网络
- 作者:未知
勒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1898-1967 ),比利时画家,他最初的艺术创作倾向于未来派和立体派。1925年加入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行列。在巴黎生活五年,与诗人艾吕雅建立了友谊。与其他强调“自动性”和“内心梦幻”的超现实主义者不同,马格利特更看重外在世界的实在物象,但他以奇特的想象给真实的物象以出人意料的变幻与转化——画布变成了窗子,树林变成了棺材,靴子变成了赤脚……带有神秘色彩的“哲理性”,令观者感到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里科对他的影响。
把我的绘画看作象征主义,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看法总是忽略了它的真正本质。……人们对物品总是从实用出发,从不在物品中寻找象征意义;可是当面对着绘画的时候,他们发现绘画毫无实用可言,于是便四处寻找意义,以使自己从困惑中解脱,因为他们不明白,面对绘画时自己究竟应当思考些什么……他们需要可以依靠的东西,这样才能感到舒适。他们需要可以牢牢抓住的安全索,这样可以使自己免于坠入空虚和茫然之中。寻找象征意义的人们,未能把握物象中固有的诗意和神秘感。毫无疑问,他们感受到了神秘感,但他们竭力想摆脱这种神秘感。他们惧怕它。通过询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表达出一个愿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有人不拒绝这种神秘感,他一定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他追索另外的东西。
形象必须呈现出原来状态。况且,我的绘画无意于使“不可视超过可视”(藏在信封里的信不是不可视的,被树丛遮掩的太阳也不是不可视的)。心灵爱恋不可知的东西。心灵爱恋那些具有不可知的意义的形象,因为心灵自身的意义也是不可知的。心灵并不理解它自己的存在理由,无须去理解(或者如何理解,理解什么),因为它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没有存在的理由。
我们有关这个世界及其对象的常识,并不足以证明它们在绘画中所应有的表现;绘画中的对象,其所具有的赤裸裸的神秘感,也许会像在现实中一样悄然离去而不为人注意。……如果某个观众发现我的绘画是在蔑视“常识”,那他的确意识到了某种显而易见的东西。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就是对常识的蔑视。
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得某人——也许他的确想开个玩笑——送给我一本未来派绘画展览图录。真要感谢这个玩笑,使我对一种新画法也熟悉起来。并且在一种真正的陶醉状态里,我着手创作车站、节日和城市的热闹场面;在这些场面里,有一个来自墓地的女孩儿——我把她与我的绘画新发现相联系——正经历着难以预料的冒险。不用说,一种纯粹的、强有力的情感——性欲,使我在那时避免了陷入对形式完美的较为传统的追求。我真正所想要的是引起情绪上的惊骇。
我们常常把相似性加给那些也许有、也许无共同本质的事物身上。我们说:“好像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我们也同样随便地说:“虚假与真实相似”。这种所谓的相似性只存在于比较中的联系;联系的相似,只有在心灵进行观察、估价、比较时,才为心灵所感受到。……相似性既与“同常识一致”无关,也与“违背常识”无关;它仅仅和由外部世界那里依据灵感所赋予的原则聚合起来的形态有关联。
近来,一种长期流行的蠢举以一个假想出现了,这个假想以为,绘画正在为一种被称为“抽象”、“非再现”,或者“非传统”的所谓艺术所代替;这种艺术就是“平面”操纵“材料”,再加上一些可以使人接受的奇想。但是,绘画的功能是创造有形的诗,而不是把世界降低到大量的物质主义方面去。
把我的绘画看作象征主义,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看法总是忽略了它的真正本质。……人们对物品总是从实用出发,从不在物品中寻找象征意义;可是当面对着绘画的时候,他们发现绘画毫无实用可言,于是便四处寻找意义,以使自己从困惑中解脱,因为他们不明白,面对绘画时自己究竟应当思考些什么……他们需要可以依靠的东西,这样才能感到舒适。他们需要可以牢牢抓住的安全索,这样可以使自己免于坠入空虚和茫然之中。寻找象征意义的人们,未能把握物象中固有的诗意和神秘感。毫无疑问,他们感受到了神秘感,但他们竭力想摆脱这种神秘感。他们惧怕它。通过询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表达出一个愿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有人不拒绝这种神秘感,他一定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他追索另外的东西。
形象必须呈现出原来状态。况且,我的绘画无意于使“不可视超过可视”(藏在信封里的信不是不可视的,被树丛遮掩的太阳也不是不可视的)。心灵爱恋不可知的东西。心灵爱恋那些具有不可知的意义的形象,因为心灵自身的意义也是不可知的。心灵并不理解它自己的存在理由,无须去理解(或者如何理解,理解什么),因为它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没有存在的理由。
我们有关这个世界及其对象的常识,并不足以证明它们在绘画中所应有的表现;绘画中的对象,其所具有的赤裸裸的神秘感,也许会像在现实中一样悄然离去而不为人注意。……如果某个观众发现我的绘画是在蔑视“常识”,那他的确意识到了某种显而易见的东西。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就是对常识的蔑视。
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得某人——也许他的确想开个玩笑——送给我一本未来派绘画展览图录。真要感谢这个玩笑,使我对一种新画法也熟悉起来。并且在一种真正的陶醉状态里,我着手创作车站、节日和城市的热闹场面;在这些场面里,有一个来自墓地的女孩儿——我把她与我的绘画新发现相联系——正经历着难以预料的冒险。不用说,一种纯粹的、强有力的情感——性欲,使我在那时避免了陷入对形式完美的较为传统的追求。我真正所想要的是引起情绪上的惊骇。
我们常常把相似性加给那些也许有、也许无共同本质的事物身上。我们说:“好像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我们也同样随便地说:“虚假与真实相似”。这种所谓的相似性只存在于比较中的联系;联系的相似,只有在心灵进行观察、估价、比较时,才为心灵所感受到。……相似性既与“同常识一致”无关,也与“违背常识”无关;它仅仅和由外部世界那里依据灵感所赋予的原则聚合起来的形态有关联。
近来,一种长期流行的蠢举以一个假想出现了,这个假想以为,绘画正在为一种被称为“抽象”、“非再现”,或者“非传统”的所谓艺术所代替;这种艺术就是“平面”操纵“材料”,再加上一些可以使人接受的奇想。但是,绘画的功能是创造有形的诗,而不是把世界降低到大量的物质主义方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