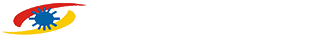《红楼梦》超现实的艺术表现手法
- 时间:2021-05-15 14:54
- 来源:网络
- 作者:王平
《红楼梦》虽然是一部写实小说,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又常常运用超现实的神秘思维方式,借助神鬼灵异等佛道观念,来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性格,创造出真幻结合、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小说开头,便运用女娲补天的神话,赋予宝玉一个顽石的前身。接着,一僧一道携石而去,历经几世几劫之后,顽石又重回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上面字迹分明,记载着它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这种奇异的开局方式与道教观念密切相关,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从叙述方式上看,又近乎所谓的“倒叙”,透露出全书结局的端倪。在此后的情节发展中,顽石的本性与宝玉的性格如影随形;一僧一道突兀而来,突兀而去,引导故事向纵深发展。
在甄士隐的梦中,一僧一道讲述了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一段情缘,为下文宝黛缠绵悱恻而又磕磕碰碰的爱情,罩上了一层“木石前盟”的奇幻外衣,暗示了黛玉对宝玉的爱情是为了偿还灌溉之情,一旦泪水流尽,爱情即以悲剧结束。僧道二人对士隐叮嘱道:“到那时不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后来,士隐听了道人的《好了歌》,心下大悟,断然离家修行。这实际上,已为宝玉的遁入空门作了铺垫。
秦钟病危之际,宝玉前来探视,为了突出两人的情谊,小说借用了佛教关于地狱的观念。秦钟挂念家事求告鬼判宽限一会儿,“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但一听说宝玉来了,都判官“先就唬慌起来”,“众鬼见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都判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于我们。”都判道:“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众鬼听说,只得将秦钟之魂放回,宝玉终于与秦钟得以诀别。
晴雯是一个气质高洁的女性,她临终之时笑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主。……我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来召请,岂可捱得时刻!”宝玉听了小丫头的讲述后忙道:“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个神,一样花有一位神之外还有总花神。”小丫头信口说晴雯是专司芙蓉的花神,宝玉去悲而生喜,乃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掌,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虽然超出苦海,从此不能相见,也免不得伤感思念。”于是,便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芙蓉女儿诔》。借助道教神仙之说,既赞美了晴雯的冰心玉质,又表现了宝玉与晴雯的心心相印。
尤三姐是《红楼梦》中一位刚烈高洁的女性。为了刻画这个人物形象,小说再次借用了佛道的有关观念。柳湘莲眼见尤三姐已经自刎而死,恍惚中又见尤三姐从外而入,向他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别,故来一会,从此再不能相见矣。”湘莲不舍,还欲再问时,尤三姐道:“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误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湘莲警觉,似梦非梦,“旁边坐着一个跏腿道士捉虱”。湘莲问道士:“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就这样,“湘莲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竟自截发出家,跟随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这就使尤三姐、柳湘莲的爱情悲剧染上了空幻的色彩,进而突出了全书的主旨。
为了暴露封建贵族家庭内的嫡庶之争,揭示赵姨娘的险恶歹毒,小说让马道婆用道教法术——魇魔法使宝玉、凤姐中魔。就在宝玉将死未死之际,癞头和尚、跛足道人突然出现,解救了这场危难。癞头和尚摩弄那块玉石时念了两段诗,即“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未通灵之前,无喜无悲,通灵之后却招来了是非。要想从梦中醒来,必须揩净粉渍脂痕,走出绮栊环境。当冤孽偿清之时,也就是散场之日。这些佛教观念,都在预示着全书的最终结局。
脂砚斋曾如此评论《红楼梦》的神鬼怪异之处:“《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耶?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的确,曹雪芹不是在“认真说鬼话”,但也不仅仅是“故意游戏之笔”。他是极严肃地借助佛道教义观念,来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以表明自己的创作主旨。只有全面把握了《红楼梦》与佛道文化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这部伟大的古典名著。(王平)
小说开头,便运用女娲补天的神话,赋予宝玉一个顽石的前身。接着,一僧一道携石而去,历经几世几劫之后,顽石又重回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上面字迹分明,记载着它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这种奇异的开局方式与道教观念密切相关,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从叙述方式上看,又近乎所谓的“倒叙”,透露出全书结局的端倪。在此后的情节发展中,顽石的本性与宝玉的性格如影随形;一僧一道突兀而来,突兀而去,引导故事向纵深发展。
在甄士隐的梦中,一僧一道讲述了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一段情缘,为下文宝黛缠绵悱恻而又磕磕碰碰的爱情,罩上了一层“木石前盟”的奇幻外衣,暗示了黛玉对宝玉的爱情是为了偿还灌溉之情,一旦泪水流尽,爱情即以悲剧结束。僧道二人对士隐叮嘱道:“到那时不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后来,士隐听了道人的《好了歌》,心下大悟,断然离家修行。这实际上,已为宝玉的遁入空门作了铺垫。
第五回关于太虚幻境的描写,在全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主要人物的命运作了暗示,对情节发展及最终结局作了交待,可以说是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太虚幻境的创造,正是借助了佛道观念。“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显然,这正是道教所追求的“仙境”。在这仙境之中,生活着警幻仙姑等一班仙女,她们“荷袂蹁跹,羽衣飘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她们的名号也都与佛道有关:痴梦仙姑、钟情大士、引愁金女、度恨菩提。警幻仙姑受荣宁二公剖腹深嘱,特引宝玉“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希望他“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宝玉留恋儿女之情,忽至险恶之处,警幻仙姑命他作速回头,因为前面即为迷津。佛教认为,三界六道都是迷误虚妄的境界,故称“迷津”。芸芸众生皆陷溺于迷津之中,须赖佛教教义,觉迷情海,慈航普渡。警幻仙姑话犹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这些描写,暗示了宝玉所要经受的种种磨折和打破情关的结局。

还有“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的风月宝鉴,一面为美女,一面为骷髅。这面风月宝鉴,乃是佛教“不净观”与道教法术相结合的产物。它由警幻仙姑所制,由跛足道人掌管,可以疗救心存妄念的生命垂危者。按照佛教“不净观”的教义,只要将美女视为骷髅,就可去掉邪念淫欲,就可济世保生。可惜贾瑞至死未能醒悟,结果命归黄泉。世人不谙此理,反而归罪于宝镜,要架火来烧。只听镜内哭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这面风月宝鉴,充分体现了《红楼梦》以佛道观念进行艺术构思的特征。
秦钟病危之际,宝玉前来探视,为了突出两人的情谊,小说借用了佛教关于地狱的观念。秦钟挂念家事求告鬼判宽限一会儿,“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但一听说宝玉来了,都判官“先就唬慌起来”,“众鬼见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都判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于我们。”都判道:“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众鬼听说,只得将秦钟之魂放回,宝玉终于与秦钟得以诀别。
晴雯是一个气质高洁的女性,她临终之时笑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主。……我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来召请,岂可捱得时刻!”宝玉听了小丫头的讲述后忙道:“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个神,一样花有一位神之外还有总花神。”小丫头信口说晴雯是专司芙蓉的花神,宝玉去悲而生喜,乃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掌,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虽然超出苦海,从此不能相见,也免不得伤感思念。”于是,便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芙蓉女儿诔》。借助道教神仙之说,既赞美了晴雯的冰心玉质,又表现了宝玉与晴雯的心心相印。
尤三姐是《红楼梦》中一位刚烈高洁的女性。为了刻画这个人物形象,小说再次借用了佛道的有关观念。柳湘莲眼见尤三姐已经自刎而死,恍惚中又见尤三姐从外而入,向他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别,故来一会,从此再不能相见矣。”湘莲不舍,还欲再问时,尤三姐道:“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误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湘莲警觉,似梦非梦,“旁边坐着一个跏腿道士捉虱”。湘莲问道士:“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就这样,“湘莲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竟自截发出家,跟随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这就使尤三姐、柳湘莲的爱情悲剧染上了空幻的色彩,进而突出了全书的主旨。
为了暴露封建贵族家庭内的嫡庶之争,揭示赵姨娘的险恶歹毒,小说让马道婆用道教法术——魇魔法使宝玉、凤姐中魔。就在宝玉将死未死之际,癞头和尚、跛足道人突然出现,解救了这场危难。癞头和尚摩弄那块玉石时念了两段诗,即“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未通灵之前,无喜无悲,通灵之后却招来了是非。要想从梦中醒来,必须揩净粉渍脂痕,走出绮栊环境。当冤孽偿清之时,也就是散场之日。这些佛教观念,都在预示着全书的最终结局。
脂砚斋曾如此评论《红楼梦》的神鬼怪异之处:“《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耶?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的确,曹雪芹不是在“认真说鬼话”,但也不仅仅是“故意游戏之笔”。他是极严肃地借助佛道教义观念,来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以表明自己的创作主旨。只有全面把握了《红楼梦》与佛道文化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这部伟大的古典名著。(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