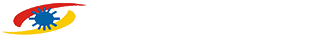母亲节里思母亲
- 时间:2024-05-07 17:09
- 来源:会员中心
- 作者:郭进拴
母亲节到了。
一大早起床,我静坐书房,凝望着母亲站在一丛苍松间的彩照,脑海中更是波涛起伏,思绪万千,思母念母之情如潮水奔涌,无休止地叩打着我记忆的闸门。
我于1958年5月出生在豫西伊川县白沙公社一个叫焦沟的贫穷小山村。母亲一生共生了12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我在男孩中排行老大。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家徒四壁”和“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家孩子那么多,一人一张嘴就是无底洞啊!
因我上边两个哥哥都没成人,母亲就给我起了进拴的名字,进表示大跃进,也有向前进的意思,拴表示拴住,不能让我再被阎王爷叫走了。在那吃大锅饭的年月,母亲喝稀汤,把碗底的稠饭让我吃。从小娇生惯养,使我从小就爱和人打架,为母亲挣了不少骂。有一次和一个贫农成份的小孩子打架,我往地下堆起一个墓古堆,提着人家爹的名字哭;人家也堆起了一个墓古堆,提着我娘的名字骂。我说:“大旺,大旺,吃的多了上不去坑。”人家骂:“冯银,冯银,狗肺狼心!”这时人家爹来了,上去先给我煽了两耳光,又骂道:“你地主羔子还想变天哩!告诉你,这不是旧社会,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天下!”这是因为我爷爷跟着他舅家享过几天福,被划为地主成份。其实我母亲是贫农,我父亲是下中农成份。因文革中我爷爷怕挨批斗,就偷偷跑到了洛阳我四叔那里,我父亲替爷爷开过几次四类分子会,人家就把我也叫成了“地主羔子”。全大队学校开会,有人专门点名把我清出会场后,再念文件,我这个才只有8、9岁的小孩子也成了“黑五类”。
母亲受不了这种气,为了我们的前途,她决定把我们在山北的一院房子卖了,领着我们从伊川迁回了汝州老家,使我们也成了下中农的好成份,从此不再受人欺侮。这不禁使我想到了孟母择邻、岳母刺字这些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故事。母亲为了我们的前途和命运,费尽了心血。可我却从小到大没少惹母亲生气。小时候,我曾从家里偷了一口袋麦子到河边种地玩,被告发后,母亲说:“你拿的麦子最少能值5毛钱,要买盐能买3斤,能维持咱全家两个多月,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母亲说话时眼里含着泪。
母亲养大了我们8个儿女,这辈子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罪。母亲是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没读过一天书。但母亲的的确确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就是凭着那双小脚、那副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务劳作,还要整天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为全家的事情费尽心思,这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
从睁开眼来到世上,跳出襁褓,到唱着歌,抹着泪,闯过青年的最后一道门槛,从我自己变成父亲,直至两鬓霜白,我仍然需要母亲,记忆里最美的女神仍然是母亲。母亲之爱将陪伴我走过一生……
母亲是伟大的永恒,其影响深入灵魂,且直到永远……
母亲生于1928年,战争年月,为避兵乱,背井离乡,四处逃难;三年自然灾害,吃糠咽菜,两腿浮肿;十年浩劫,又饱尝了苦难风霜。我的母亲一生都在乡下,她过不惯城里人的生活,在我这里住不上三、五天,就想家,就头疼脑热。一回到乡下,和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在一起烧烧香,念念经,赶赶庙会,就会百病皆除。每当我工作失意,受了委屈时就想到了母亲,就想当着她的面哭诉一场,母亲是我人生和事业的加油站。
母亲姓冯,叫银,我最早见到这个名字,是上小学时在生产队的记工本上,那封面写着母亲的名字,里边记录着母亲每天、每月的出工情况,以及月小计、季合计、年累计。那时候,母亲虽是女劳力,却比有的男劳力挣的工分还要多。她白天忙完队里的农活,夜晚就坐在煤油灯下纺花、织布,给我们做鞋子、缝新衣,那一针一线凝聚着母亲深深的情和爱。此情此景,不由使我想起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古老诗句。
1974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我那年仅47岁的父亲与世长辞了,那天离我的16岁生日还差5天,父亲走的太急,没能等到这一天。
那是个撕心揪肠的日子。父亲从病情恶化起,就不会说话,浑身火炭似的发烧,烧干了心胸腔里的滴滴血汗。那天傍晚,我给父亲注射了一支强心针,实指望他能熬过这一夜。可到了11点多钟,父亲眼里突然有了泪水,望着我,嘴张了几张,似乎想说什么,可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是我们家的天,天塌了!父亲是我们家的地,地陷了!当时我最小的妹妹才只有1岁,还不省人世。我那白发苍苍的爷爷也从山北赶了回来。老人家捶胸顿足,失声恸哭:“儿娃!老天爷太不公道了,我还没死咋会轮到你哪!老天爷啊!你咋不睁睁眼,让我替儿去死啊!如今,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惭啊!呜呜呜……”爷爷泣不成声,哭昏了过去。
父亲从7岁起就开始跟着我老外爷放羊,他赶着羊群经常路过我外婆家门口,后经人介绍才和我母亲成了亲。他靠着一把羊鞭,供我的4个叔叔、1个姑姑上学读书,成家立业。后来又和母亲养活我们8个儿女,他一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的福,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正当壮年,却显得非常苍老,脸上的皱纹就像黄土地上的沟壑一样,饱经了风霜,历尽了沧桑……父亲是被活活累死的!
父亲走后,母亲夜里泪湿枕,人前忍悲意志坚。既当爹来又当娘,千斤重担一人担。她春天上山采野菜、树叶,晒干存起来让我们冬天吃;夏天收罢麦,就到地里捡麦子;秋季下地拾坏红薯圪瘩;冬天纺花、织布,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饱穿暖。稠饭先让孩儿吃,娘喝稀汤吃剩饭。好衣让给孩儿穿,娘衣补丁连成串。一床破被三十年,养鸡下蛋换油盐。
做为我们4兄弟的老大,我决定接过父亲的放羊鞭,为母亲分点忧。我上山放了半年羊后,母亲却支持我上高中,说:“孩子!去上学吧,你爹这辈子就吃了不识字的亏,家里还有我哪!”
我于1974年秋季经贫下中农推荐到离家18里的临汝镇上高中,母亲为我缝制了新被褥,棉花垫得极厚,总害怕把我冻着。冬天母亲又为我缝了黑土布新棉衣和窝窝棉帽。有一次,班主任王松寿老师摸着我的窝窝帽子说:“真是农民的儿子,还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啊!”满教室的学生都望着我笑。我说:“王老师,这帽子挺暖和的,您如果想戴,我也叫俺娘给您缝一顶!”王老师忙说:“不用,不用!”母亲怕我吃不饱,经常给我送花卷馍和山野菜。有一次母亲天不亮就背着一袋馍给我往学校送,不小心滑进了路边的水沟里,被过路人发现后费了好大劲才把母亲拉出来。当母亲一瘸一拐地赶到学校时,我还没有起床呢。
1975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家背粮饭时见母亲躺在床上,两只脚脖肿得像虚糕馍。一问才知是母亲为生产队割草时,不慎从崖上跌了下来,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竟交待我二姐给我送馍时不要说跌伤的事。我望着母亲,放声大哭了起来。母亲却用手给我擦着泪说:“不要紧,过几天就好了!”后没等伤痊愈,就又瘸着腿去割草挣工分去了。
高中毕业后,我迷上了写作,起初母亲怕我惹出乱子,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就不理解、不支持,曾点火烧了我写的一大摞百投不中的稿子,可我竟砸了我家的饭锅,摔了我家的饭碗。气得母亲哭了几天几夜,水米未进……我也从此离别故乡,到了洛阳、郑州等地四处流浪,也发誓写作不成功,就一辈子不回家门,宁愿死在外边喂野狗。到了1979年寒冬的一天,母亲一次收到了两张稿费汇款单,就有意拿着这两张稿费单到人多的地方去“炫耀”,她一边让人看,一边说:“俺栓娃子来钱了!俺栓娃子来钱了!”识字的人一看是稿费,纷纷夸赞:“这孩子有志气,发财了,成事了!”从此,母亲天热给我煽扇子、赶蚊子,天冷给我做暖靴,全力支持我写作,省内外报刊上也接连出现了我的名字。
我曾于1992年和1997年两度分别到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母亲听说后,动员我的二弟、三弟给我筹集了4000元学费,亲自缝到自己的内衣口袋里,走了18里山路,又坐公共汽车到我当时工作的汝州城里,硬是把钱交给我,又千叮咛、万嘱托,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每次上学走,母亲总是把我送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家。
在1994年我的36岁本命年到来之际,我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了20个春秋的愿望——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的地方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发了消息,老母亲看了一遍又一遍,还让识字人念报纸给她听,边听边看边流泪,她比我还高兴哪!她嘴里不停地说着:“我栓娃子可是老不容易啊!”
自从我于1980年参加工作后,先是在临汝镇文化站工作,又于1986年调到汝州市文联,2000年调到平顶山市文联工作。母亲每次到我家,总要带些绿豆、芝麻、山野菜之类。走时什么也不要,就要几本我新出的书,回去除送亲朋好友外,还把我书中写的歌谣,剧本中写的唱词,让识字的人教会了当成经念,并经常在一些庙会、节日和一群老太太在一起唱我写的歌谣、唱词。还爱到处宣扬说:“这是俺栓娃子写的!”母亲的嗓音很好听,唱得也很动情。母亲每次到寺庙烧香,都祈求我写出名堂,祈求孙娃子能考上好大学。
我母亲是个勤劳、坚强、勇敢,有志气、有毅力的人。她一生曾搬过8次家。先是我们家穷,住不起房子,就住在村西自己打的窑洞里,据说我父母就是在窑洞里结的婚。后盖了三间草房,我叔叔结婚时,父母让出了草房,搬到村东头借住别人家一间破房。好不容易在村中间盖了三间瓦房,又因学校要占,我们又搬到了沟北的寨子上,刚又盖了几间房子,因我和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欺侮,母亲又决定从山北迁回了汝州老家,平地起古堆,又盖了一院新房,花完了多年积蓄;可好景不长,队里又要建新村,又一次搬家,接着又为我们四兄弟一一娶妻成家,又每人盖了一处宅院。母亲为我们8个儿女操碎了心!受够了累!
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我本应该为这个家多操些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可我的母亲一辈子操劳惯了,她不愿过城市生活,70岁那年还承包着责任田,经常下地劳动,还把我给她的零花钱,买成猪娃和羊羔在家里喂着,喂大了再卖了换成钱,逢年过节就发给孙子、孙女和外甥们,作为压岁钱。
母亲给我们的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三弟小时候一只脚歪着,不能走路,母亲就用她那双温柔的手,硬是数年如一日,终于把三弟的脚捏正了,揉好了。母亲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悲伤,在我父亲病故后,我的舅舅、外婆、舅母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相继去世,是母亲一手给他们办的丧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爷爷和奶奶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不幸病故,真是一个悲痛连着一个悲痛。母亲为此流干了眼泪,累瘦了身子,洒尽了血汗。
我的母亲从小就给了我足够的、真挚的爱。每每有吃宴席之类的好事,母亲总是偏心地把两个姐姐打发到一边,带着我去。家里有好吃的,总是尽着让我先吃。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因忙于组织镇里的春节文化活动,腊月二十三没顾上回家,母亲还把她烙的发面火烧一直给我留到年二十九我回家时才给我。我咬着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火烧,两眼含满了热泪。我调到平顶山后,母亲每年都要跑几百里给我们送来了老家院子里长的石榴、核桃、苹果和母亲亲自种的花生、嫩玉米、红薯和老窝瓜。可怜天下慈母心啊!也正是这种温柔动人的爱,从小就渗透在了我的心田里,成为我思想和行动的一种善良的出发点。
母亲敬有观音菩萨塑像,大慈大悲,积德行善。她听说洛阳我四叔重病在身,需要老家亲人去把“鬼”引回来,就只身去洛阳“引鬼”,回来就得了重病,经检查是癌症。当时我不信,就接母亲来到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确诊。当得到母亲癌症晚期的结论时,我一下子懵了。在医院抢救到腊月二十三,娘执意回家过年,谁知从此母子别,锥心泣血肝肠断。
严父早逝恩未报,慈母别世恨终天。鸡年正月二十九,当我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时,正在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平顶山市委召开的党员大会分装会议文件和学习资料,并将我新出版的《洪流滚滚》一书也分别装到了每个党员的文件袋中。当我忙完这一切,急急忙忙往家赶的途中,手机中传来了弟弟的哭声:“哥!娘走了……”得知母亲已等不到我,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的消息,我顿时如五雷轰顶,手机“啪”地一声掉到了汽车上……当看到操劳一生、干瘦如柴,临终又不得我祭的母亲,我泪如泉涌,跪地恸哭。真是依依叩送泣花钿,母容依稀在眼前。缝补灯前留瘦影,纺车月下晃寒烟。长恨生前行孝少,常思慈母永难见。
大人物之所以大人物,是因为名字被千万人呼喊的结果,母亲的名字我至今没有叫过,但母亲不是大人物却并不失去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
每当我坐在书桌前写作的时候,一抬头就会看到母亲的照片:她沉静、美丽、慈祥、善良,她给我力量,给我智慧,给我勇气,给我信心!有母亲陪伴,无论多重的担子,我都敢挺起腰板挑上肩去!无论多远的路程我都敢一步一步从头迈起!
我为有这样伟大而坚强的母亲而骄傲,而自豪!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