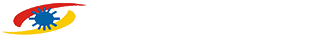作文描写:希冀
- 时间:2021-08-04-09-49
- 来源:网络
- 作者:佚名

《风景》赵暄妍 9岁 选自《少儿画苑》国际少儿书画大赛
觉新走出水阁,一个人在玉兰树下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他好象渴望着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就在他的眼前,但是他知道他不会得到它。他感到空虚,感到人生的缺陷。他痴痴地靠着树干,望着眼前的一片新绿出神。树上响起了鸟的叫声。两只画眉在枝上相扑,雪白的玉兰花片直往他的身上落,但是过了片刻又停止了。他看见两只乌向右边飞去,他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恨不得自己也变作小鸟跟它们飞到广阔的天空中去。他俯下头看他的身上。几片花瓣从他的头上、肩上落下来,胸前还贴了一片,他便用两个指头拈起它,轻轻地放下去,让它无力地飘落在地上。 (巴金:《家》第187页)
最近,她内心中萦绕着一种对男性的欲念。这并非生理上的原因,而是成天和秀兰在一起,觉得自己精神很空虚。她绝不是渴望着结婚!如果是那样没意思的女人,她不会抗婚三年,终于达到解除婚约的目的。她是觉得她那么需要和秀兰一样,想念着一个男人,而又被一个男人所想念——这个男人给她光荣的感觉,是她心上的温暖和甜蜜!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50页)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104页)
夜是温暖的,似乎异样静寂,好象宇宙万汇都在谛听着,期待蓿;而伯尔森涅夫,被包围在这无边的静夜里,就不自主地停立了;他也开始来谛听,期待。从近处的树梢不时有轻微的飒飒声传来,有如女人的裙裾的悉索,在伯尔森涅夫的心里唤起了一种似甜而又似难受的感觉,元乎近于恐怖。他的面颊感觉着微微的痉挛,一丝眼泪使他的眼睛感觉着寒凉:他宁愿完全无声地走过,在黑暗中蹑足摸索。一阵横风忽然向他袭了过来——他微微抖了一抖,于是,悚然驻立;一只沉睡的甲虫从枝头跌下来了,铿然落在路径上面;伯尔森涅夫不禁低低“哦”了一声,于是,又一次地停止了。可是,当他一想起了叶琳娜,所有这些瞬间的感觉就立刻消逝了,所留下的只是由暗夜的清静和夜行的寂寞所产生的新鲜的印象;而一个少女的面影就浮现在他的整个灵魂里来了。 ([俄]屠格涅夫:《前夜》第27--28页)
这一天,在叶琳挪看来,过得很慢,那悠长的、悠长的夜,尤其是过得迂缓。叶琳娜有时坐在床上,两手抱膝,头也支在膝上;有时,她又走向窗前,把燃烧的前额紧贴着寒冷的玻片,想着,想着,把同样的思想反复想着,直到自己完全疲倦。她的心并不曾确然变作了化石,也不曾从她的胸腔消逝,可是,她却已经不能感觉它的跃动了;只有热血在她的脑里苦痛地汹涌着,她的头发令她感觉火热,嘴唇已经烧得拈焦。“他会来的……他还没有跟妈妈辞行……他不会欺骗……难道安得菜·彼得罗维奇的话是真的?那是不会的。……他没有用言语答应他会来。……
难道我会和他永别了么?”——这种种思想从来不曾离开过她,实实在在地不曾离开过她;它们并不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只是在她的脑里一直盘旋,如同一团迷雾。“他爱我!”——这思想忽然闪光似的掠过了她的全身,于是,她就直直地凝注着黑暗;一抹秘密的、谁也看不见的微笑,使得她的嘴唇分开了。 ([俄]屠格涅夫:《前夜》第109页)
我觉得处处都有一种不安的兴奋——那种兴奋在我的心里也越来越强了。我靠在船边上。我耳边的微风的絮语、船尾下面河水的轻柔的潺潺声使我感到烦躁,波浪的清凉的气息并不能使我冷静下来。一只夜莺突然地在岸上唱起来了,我感染到它那歌调的甜蜜的毒素。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来了,但是这并不是空泛的、快乐的眼泪。现在我所。感到的已经不是那种模糊的、不久以前当我心灵舒展、歌唱、而且觉得它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爱着的时候,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无所不包的渴望的感觉……不,幸福的渴望在我心里燃烧着。 ([俄]屠格涅夫:(《阿霞》《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218页)
她希望养一个儿子,身沐结实,棕色头发,名字叫做乔治:她过去毫无作为,这种生一个男孩子的想法,就象预先弥补了似的。男子少说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周游天下,克服.困难,享受天涯海角的潦乐。可是一个女人,就不断受到阻挠。她没有生气,没有主见,身体脆弱不说,还要处处受到法律拘束。她的意志就象面网一样,一条细绳拎在帽子上头,随风飘荡。总有欲望引诱,却也总有礼防限制。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87页)
他老想着戏:上半星期想着过去的戏,下半星期想着下次的戏。他甚至怕上演的那天害病;这种恐惧使他常常觉得有三四种病的征象。到了那天,他吃不下饭,好象担着重大的心事,骚乱不堪,跑去对时钟看了几十次,以为天不会黑的了。临了他忍不住了,在售票房开门以前一个钟点就出发,怕没有位置’又因为他第一个到,对着空荡荡的场子不免暗暗发急。祖父和他说过,有两三次因为看客不多,演员宁可退还票价而停演。他注意来的人,数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噢!不够啊……人数老是不够啊!”看到花楼或正厅里来了几个重要的人物,他心又轻松了些,对自己说;“这一个,他们总不敢请他回去吧?为了他,总得开演吧!”——可是他还没有把握,直到乐师们进了场才放心。但他在最后一刻还在发急,不知道会不会开幕,会不会象某一晚那样临时宣布更改戏码。他山猫似的小眼睛瞅着低音提琴手的乐谱架,瞧瞧谱上的题目是不是当晚演的戏。等到看清楚了,过了两分钟又看一下,只怕刚才看错了……乐队指挥还没有进场,一定是害病了……幕后有人忙忙碌碌的乱做一堆,又是谈话声,又是急促的脚步声。可是闯了祸,出了事吗?还好,声音没有了。指挥已经在他的位置上。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还不开场!是怎么回事呢?……他急坏了。——终于开演的记号响了,他的心跳了。乐队奏着序曲;然后,克利斯朵夫有几个钟点在极乐世界中载沉载浮,美中不足的就是担心这境界早晚要完的。([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81—82页)
晚饭后,本拟趁早睡去,以便迎接次日更沉重的劳作。奈天色尚早,暂倒在藤躺椅上,闭目沉思。首先涌上心头的是:晚班邮件快来了,上海的信该来了。
恰在这时,忽然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心想:准是迫不及待的邮人,准是信来了,准是上海的信来了。但接着敲门声,却没有照例的嘹亮而拉长的一声:“信——”
虽然如此,我总相信这是邮人,是信,是上海的信,是我所期待的
信。我向来总相信这经验:他丝毫不苟,信到必复,复信往往可计时收到,绝少例外。 (曹靖华:《望断南来雁》《飞花集》第223页)
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象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巴金:《怀念肖珊》《烟火集》第270页)
他会是什么模样?我久久凝视玫瑰的花瓣,欢愉地抚摸它们:我希望他的小脸蛋象花瓣一样娇艳。我在盘缠交错的黑莓丛中玩耍,因为我希望他的头发也长得这么乌黑卷曲。不过,假如他的皮肤象陶工喜欢的粘土那般黑红,假如他的头发象我的生活那般平直,我也不在乎。
我远眺山谷,雾气笼罩那里的时候,我把雾想象成女孩的侧影,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因为也可能是女孩。
但是最要紧的是,我希望他看人的眼神跟那人一样甜美,声音跟那个人对我说话一样微微颤抖,因为我希望在他身上寄托我对那个吻我的人的爱情。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母亲的诗·他会是什么模样》 《世界文学》1982年第5期第251-252页)
我想在我底心野,再搞拢荒草与枯枝,寥廓苍茫的天宇下,重新烧起几堆野火。
我想在将天明的我的生命,再吹超我嘹亮的画角,重招拢满天的星,重画出满天的云彩。
我想停唱我底挽歌,想在我底挽歌内。
完全消失去我自己,也完全再生我自己。
(潘漠华:《再生》《新诗选》第一册第298页)
泪珠儿要流尽了,爱人呀,还不回来呀?我们从春望到秋,从秋望到夏,望到水枯石烂了!爱人呀,回不回来呀?……我们为了他——泪珠儿要流尽了,我们为了他——寸心儿早破碎了。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你们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
时间一手将我所有韵都偷跑了,只留下了哀悔。
时间好似狂风,连号带唉,将我的生命偷跑了;我所有的残余,只是哀悔。
当我在安逸快乐时,她轻轻地向我软语缠绵,使我不能从迷茫中振起——似一只湿了翼的小鸟,伏居在温暖韵香巢。
我一听了她甜蜜的美妙的脚声,如飞丝般绕人心轮,就渐渐睡了去。
但当我醒了时,一切都被时间偷走了;我所有的,现在,只是哀悔,只是哀悔。 (焦菊隐:《时之罪恶》《新诗选》第一册第438页)
[远处猛风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