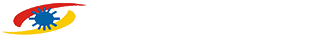郁达夫小说浅论
- 时间:2023-09-16-16-51
-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郭进拴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十七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岛丛林。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郁达夫一共写了《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中期:1933年-1938年。这个时期,是郁达夫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流连往返于山林江湖。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郁达夫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
1921年初版的小说集《沉沦》中的三篇小说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后的结晶,标志着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特有的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新形态的浪漫主义的形成。而另一方面郁达夫其人其文也确实遭受了相对较多的误解。因为郁达夫小说对性欲的描写对于同时代的大部分评论者来说,过于前卫。所以郁达夫的小说在当时被指责为诲淫。而这种思维定式在很长时间里也影响了后来批评家对郁达夫小说的判断,压抑了郁达夫研究的发展,比如郁达夫作品的搜集整理,迟至80年代以后才开始。所以郁达夫研究中许多问题看似不成问题,许多问题看似已有结论,但是如果用新的材料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位百年前的作家,还是能得到一些新的结论,收获意外之喜。这是郁达夫研究的魅力。
杨斌教授的《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离愁》一书的写作动机和目标也是如此——正如作者夫子自道:“正是因为郁达夫的有趣,真是因为郁达夫生前死后的褒贬,正是因为郁达夫若干至今未解的谜团,激发了笔者对他的兴趣。这本书,可以说,就是为了破解郁达夫的许多不解之谜,也是笔者对郁达夫之同情和理解。”正因为是从兴趣出发,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郁达夫传记,也不是学术论文集。而更像是历史学家杨斌教授对郁达夫的阅读札记。既有学术性的考证、文本分析,也有一些作者主观的感想和联想。作者对郁达夫研究是熟悉的,时时注意避免所谈内容老调重弹,书中有不少可以引起学术讨论的新颖见解。
全书分为十三章,除了第一章和第八章之外,其余十一章都围绕着郁达夫和周围人的人情关系展开。第一章十分特别,章名为《“我自己的丰采不扬”——郁达夫的“尊荣”》。从不同的章节名读者就可以看到这本书所讨论的大小问题虽然都与郁达夫的爱恨离愁有关,但并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
不同于一般的郁达夫传记从郁达夫的少年天才开始写起,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小标题就毫不客气地“攻击”郁达夫的长相“一个痩黄奇丑的面型”。作者花费了一章来充分的展开说明郁达夫的“丑”,是因为在作者看来,郁达夫的“爱恨离愁”都与他的“丑”有关:
郁达夫文采风流,但的确貌不出众。他身材瘦弱,脸颊小,眼睛小,大鼻子,颧骨突出,招风耳,相貌介乎中人或中人之下,根本不是什么美男子。以外貌而言,他和翩翩才子的形象似乎不沾边,和他早期清新的文字也差之甚远。身材和形貌的平凡成了他长期以来自卑心理的一个关键源泉,也成为长期笼罩在他和王映霞看起来人人艳羡美满婚姻上的阴影。风姿绰约的王映霞嫁给他后,郁王夫妇看起来确实是典型的郎才女貌。这对夫妻,在俗人眼中,如果别人不介绍他们是郁达夫和王映霞,从容颜上的确不大般配。而郁达夫基于相貌的不自信乃至焦虑和狐疑,在后来从杭州到湖南的流亡途中就直接爆发了出来。
杨斌教授的这个看法是很值得讨论的。众所周知,郁达夫是中国现代少有的以爱美人和敢于自白爱美人而闻名的作家。曾经写下“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样的名句。但其貌不扬的外表对这种追求造成了限制。情欲的求而不得构成了郁达夫“孤独感”的最重要部分。这种“孤独感”并非离群索居时一个人的寂寞,而是蒋晖在《孤独六讲》中讨论的让一个人成为无法合群的独特个体的那种天性。现代文学名家,几乎个个都有自己的“孤独感”,但极少有像郁达夫这样情欲问题在“孤独感”中的比重如此之大。当他在文学创作上善用这种“孤独感”时,就能创作出《沉沦》这样的名篇。但是当他被这种“孤独感”吞没时,他在文学创作的成绩就没有那么好。看郁达夫日记和各种郁达夫传记都可以发现,郁达夫在遇到王映霞之后几乎放掉所有正事,全心投入到对王映霞的追求当中。这种任性而为在现代作家中是少见的,更何况郁达夫当时已经是出名的大作家。所以杨斌教授并未明确说明的是:在第一章,他其实是想说明郁达夫的特异性。而藉由这点进入郁达夫,确实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郁达夫。而书中的其他篇章,也就是在这个角度的延长线上,探讨“这样的”郁达夫与周围人的互动关系。
文学创作中的“自叙传”色彩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其作品《还乡记》《还乡后记》和小说《迟桂花》,都运用大量内心独白式的抒情、描写、记叙,错落有致,感情真挚,打上有很深的个人印记。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首先,郁达夫强烈地表现出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调。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同,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宣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沉沦》的主人公是“他”,小说的叙事视角为第三人称叙事。一般说来,第三人称叙事是全知叙事,而《沉沦》虽然以“他”为叙事视角,但无意中加以相当严格的限制,可以视为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主人公“他”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小说讲叙的全是“他”的体验、情绪、实感,全文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所有小故事都是在“他”的意识推动下发生。小说的第一句:“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3]如果改成“他孤冷得可怜”,那么原文与改句在叙事意向上有何不同呢?两句话都写出一个事实,即“他孤冷得可怜”。但是改句突出叙事者认为“他孤冷得可怜”,而“他”自己是否认同却不确定;原文表明“他”自己认为“他孤冷得可怜”,而叙事者是否认同却不一定。“近来觉得”,即“他”感知的方式,将“他”的心理体验和主观认识纳入一种强烈的意向投射中。
“孤冷”是一种生存状态。“孤”,孤单,有两个维度。第一,就主体与环境而言,缺少同类物,所以孤单。第二,就内心体验而言,缺少理解者,所以孤单。“冷”,清冷,与“孤”的生存意向大体相同,只是用有温度的词语来表达。“孤冷”乃是一种状态,主体对这种“孤冷”的判断,则需要另外的形容词来描述;于是“可怜”一词得以出场。“可怜”表达情感价值。“可怜”的对象乃是“他”自己,因而“可怜”就表现为自我怜惜和自我安慰。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留学海外。在一般人看来,这是风光体面、实现自我价值的让人羡慕的人生。但年轻人在异域他乡生活,多少会有孤独寂寞之感,但大部分都能化解。主人公“他”的自我“可怜”,暗示在海外留学生活中遭遇了情感或意识或两者兼有的严重挫败。
因此,小说的第一句话虽然运用“他”这一第三人称呈现出全知叙事的视角,但又通过“近来觉得”这种类似于第一人称叙事加以限制。小说通过“觉得”体语句,实现了叙事权的让渡,即把隐含作者的全知叙事“让渡”给以“他觉得”为视角的限知叙事。“让渡”这一说法也并不完全准确,《沉沦》的叙事看似全知叙事,却又严格控制在限知叙事中。这种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有机融合,全知叙事仿佛一层透明玻璃,限知叙事是玻璃后的真实情景,并且清晰可见。这一叙事功能的实现,得益于“觉得”体的叙事语法。
“觉得”,说到底表现的是人的心理感知。“他”——“近来觉得”,表现的是“他”近来的心理感知。心理感知不解决“真”的问题,而是面对“意”的问题。“意”包括的是个体认知与情感体验等主观性内涵,通向存在意识。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说法,对于“他”而言,可以说“他觉得,他孤冷”。“他近来觉得孤冷”中,“孤冷”是“觉得”的结果;“他觉得他孤冷”接近“他觉得,所以他孤冷”,“孤冷”上升为谓词,成为一种独立的生存状态。“觉得”,将主人公的意向投射于自身“孤冷”的生存状态上,从而得出自我“可怜”的情感价值判断。“可怜”既是“孤冷”的延续,也是“孤冷”的平方。“孤冷”只是个体内在的自我感知,而“可怜”不仅向内怜惜自己,而且向外呼唤对自身的关注。这就可以理解《沉沦》结尾的出现,这个结尾曾让很多人不解和纠结,甚至嘲笑和讽刺。实际上,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已经注定了小说的结尾方式。
因此,“觉得”一词不仅仅引导对主人公“他”的心理感知的描述,更是在确证主人公“他”存在的方式。接下来小说描写主人公“他”感受大自然的情景与心态。“他”站在大平原内,四周是苍黄未熟的水稻,微风吹拂。“他”读着华兹华斯抒情诗,“他”被彻底感动了,一面用英语赞叹着屋瓦上的薄雾,一面涌出两行清泪。小说写道: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著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哼(疑为“喷”字之误——引者)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呆呆的”表明“他”完全沉醉其中。“他忽然觉得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觉得”是他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那么“紫色的气息”是什么样的气息?根据下文看来估计是“紫罗兰气息”。接着是“息索一响”,一棵小草打破了“他”的梦境,把“他”从沉醉中唤醒过来。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清和的早秋、澄清透明的以太,这一切环境看似写实,但都经过了“他”的“觉得”的过滤与“美颜”。“他”的陶醉,用了三种情景来描写:睡在慈母怀里,那是童年的记忆,人类的记忆,也带有现实性;“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这是中国人想象的美好乐园,中国文化特有的乌托邦;“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这是“他”所想象的西方现代生活图景。
因此,“他”“觉得”,既有中国传统的见物感怀,又能融汇西方大胆而热情表达情感的开放自由。“觉得”即是将周围世界自我化,从而让“他”的主体色彩涂抹在任何出现在“他”的眼中之物上。“孤冷”,就全篇指向小说中的苦闷,即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这就形成了《沉沦》的浪漫主义特色。
《沉沦》集中的《沉沦》和《南迁》中“觉得”一词均多次出现,这在别的小说中极不常见。“觉得”体是否可以视为郁达夫那些“自叙传”小说的内在叙事语法,还值得进一步探索。郁达夫以一种浪漫式的“我”来表征国民的主体发现,并由此而揭示和剖析民众精神病疾。与西方浪漫派意义上的“我”的主体生成历程不同之处在于,郁达夫笔下苦闷而忧郁的“我”是经过“旅行”而实现了在地化的现代主体,同时试图在社会(国家、民族、社群、集体)与主体(身体、性、意识、经验)的相互纠葛中彼此实现螺旋式上升的双重蜕变。这也是造成“现代主体”的创伤性体验的重要因由。而现代文学的“精神分析”实践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对于郁达夫而言,自叙传的形式使他能够更多地倾泻“我”的情绪和感受,将抒情主体的内心躁动和精神病疾充分展示出来;然而,对某种形式的选择(自叙传小说的形式厘定)迫使郁达夫不得不有意识地在现实中的我与虚构作品中的“我”保持距离,从而才能形成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并以此达到情感和灵魂的“净化”,这不仅是缓解现代文学作者自身焦虑的良方,而且也是现代文学得以成为置身于外的“旁观者”——精神分析者的关键所在。本文集中讨论的是郁达夫对自叙传文体这一形式的选择,他不仅将社会层面的国民集体无意识和个体的苦闷与道德困境糅合起来,由此对社会、时代、国民的精神病症加以结构,并将这些元素的聚合归入到自身的美学理想之中,在小说里体现为一种现代修辞的运用。
而“自叙传”式的现代小说修辞,也为“中国道德”提出了新的命题。现代文学所探索的“道德”问题已经被搁置了很长时间,而这所带来的弊端,在当下社会已经很显著地表现出来,并已饱尝其苦果。可以说,回到现代文学发生之初的境况,指出在旧礼教与新道德之间,并不是先破后立或者不破而立的关系,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新的价值准则和伦理要求,而是以破寓立和破中带立的方式,将新的因素化入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提供一个切中肯綮而又富于启发意义的起点,并且引入了民族国家——“中国”的维度,经过基于社会与个体两个层级的精神分析之后,为“中国道德”的再生成提供合理的空间和尺度,并通过特定的文学形式和话语形态,创造出新的想象、体悟和认同。
创作于1922年的小说《采石矶》是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别有意味的一篇,小说主要展示了“神经过敏”的黄仲则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黄仲则是一个身患“忧郁症”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有着“孤傲多疑”的性格,每当他遭遇心理抑郁和精神挫伤时,内心散发出来的深切忧郁和哀伤便形成了他的精神病症兆,恰恰是此时,挺身而出缓解其精神的却往往是文学这一药石。也就是说,只要是精神上的焦虑和苦痛一发作,文学的力量便自然而然地随之参与其中,彼此形成衬托或对应。当他遭受爱情的挫折时,“他的少年的悲哀,只成了几首律诗,流露在抄书的纸上……”当吊唁他心爱的“薄命诗人”李太白之墓时,“心里的一种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涌了起来……走回学使衙门去的时候,他的吊李太白的诗也想完成了……”当他大病初愈,顿感“无聊”,“觉得人生事事,都无长局。拿起笔来他又添写了四首律诗到诗稿上去。”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在在说明抒情主人公黄仲则似乎想通过诗歌的方式,治愈内心愤懑与灵魂焦灼。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文学诚然只是/只能以“纾解”的方式,作用于黄仲则的精神病疾,因此,可以反过来说,诗歌(文学)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药石,对内在的焦虑和纠葛能做到药到病除;更重要的是,与其作此理解,不如将蕴于小说之中的“文学性”先释放出来,因为对于郁达夫而言,文学的审美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能直接作用于现实之病痛,而回到黄仲则身上,他实则是先发现了“文学”,然后才通过文学“发现”自己。也就是说,“文学”与他的自我是一种相互缠绕和纠葛的关系——随着诗歌的吟诵、内心的吐露以及小说情节的推进,“文学”得以逐步深入到黄仲则的“精神”进行透析。
从中可以看出,文学的方式不仅是黄仲则消解忧郁和痛苦之“沉沦”的“升华”之法,而且是作者得以实现对其进行精神解剖和分析的媒介,与此同时,郁达夫实际上也通过文学的形式——尤其是自叙传小说的自“我”表现和铺陈,实现了抒情主体的精神之“解剖”,从而对包括青年知识分子在内的“小国民”的精神分裂与身体病症进行互证式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说,郁达夫代表着现代文学及其以精神分析功能为媒介实现的时代欲望的满足。文格反映人格。作家所创造出的人物,环境往往反映着作家自身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反映着作家最鲜活的灵魂。郁达夫小说的第一个特点是拥有自传的性质,郁达夫的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着他的影子,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是在日本留学,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性格热烈而又忧郁,对于原始本能之欲望既服从又羞怯,对美好的事物有着敏锐的直觉和不懈的追求(体现在郁达夫笔下人物对自然之美的感受)。表现的比较明显的是《茫茫夜》中的主人公于质夫,他不仅拥有以上的各种特点,甚至于拥有与作者相近的名字。这自传性质的小说也能够反映出郁达夫本人的心理特征。他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祖国饱受欺凌。他独在弹丸之地的异乡,却仍无奈地感受到了祖国的落后,也沉痛地意识到了落后即被歧视的事实。这对于一个正值热血时期的青年来说无异于巨大的压力与痛苦。同时他承受着独在异乡无人理解的寂寞,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忧郁而又向往着美好的。
在读郁达夫的小说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被普遍认为失败的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的女主角孙荃,郁达夫对她也是怀有深厚感情的。比如《银灰色的死》与《茑萝行》中怀恋妻子的人物形象就反映了作者对妻子的复杂的情感。他在《茑萝行》中细致地刻画了主人公与妻子相处时的情感变化,独居异乡时对妻子的思念,心情烦躁时对妻子施与的暴虐,妻子的体贴与乖巧,妻子生病时主人公的怜惜与心疼。这虽然是一篇小说但从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与经历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就是作者本人的投影。既然从这两篇文章中都可以看出作者对妻子的爱何以郁达夫最终抛弃妻子结识新欢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复杂的。郁达夫是一个受过新式开明教育的人,从他的文章中又可以看出他天性的浪漫多情。他与第一任妻子的包办婚姻使他的心里生出了反感,但婚姻又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一样的将两人捆绑的关系很难不使人生出一种羁绊的情感。两人又朝夕相处,生育了四个孩子。郁达夫独在他乡的时候能够使他怀念的他所拥有的女人也只有他的妻子。所以他对妻子必然怀着深厚感情的。然而这样的感情并不牢固,所生出的情感也只是因需要而产生的依恋,郁达夫对她没有探究的欲望,没有迷恋的情感,也就很难产生长久的爱情。于是浪漫而对爱情拥有强烈渴慕的郁达夫遇见王映霞时便成了一段新的情缘佳话。即使他对孙荃没有那么热烈的爱恋,他们终究是有感情的,于是《银灰色的死》与《茑萝行》中怀恋妻子的人物形象便跃然于纸上了。
郁达夫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私小说是日本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是由日本的自然主义发展出来的小说形式。注重对人物最真实的刻画,没有隐瞒没有遮拦的展现人物的内心。郁达夫自传式的小说写法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我最想表述的是郁达夫小说中对于欲望,情爱的大篇幅描写。郁达夫的许多小说中都对于人类最羞于启齿的性的欲望有着不避讳的描写,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对于人之本性的呼唤,是一种人性的解放。所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到的就是什么样的世界。一直以来性都是一个羞于启齿的话题,然而作为最原始的本能,性的本质其实是神圣而又美好的,它赋予了生命繁衍后代的能力,使得地球成为一个独特的拥有生命和文明的星球。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夸张的说,没有性,也便没有如今这样一个世界了。其次郁达夫在他的小说中对于爱情的发生也提出了许多在那个年代看来非常震撼的观点。如果说在《茫茫夜》中于质夫对于吴迟生的爱还只是作者委婉表述的纯粹而高尚的至高的友谊,那么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郁达夫对于同性之爱的描写可谓非常直接了。虽然这两篇文章的主旨都不是同性之爱,甚至于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对同性之爱的描写并不全是美好的,但作者所表述的爱情观却是一个极大的精神上的进步与思想的开化。文中质夫曾向往的与迟生共度的美好幻境平实感人,房前的青草,河里的游鱼,和暖的绪风,彼此守候的细节,甚至无聊时打发时间的方式都想的周密详细,即使是旁观者也不得不动容了。在当今的世界,同性之间的爱情比以前虽容易了些,总还是被许多人所不理解。而郁达夫在那样一个封建不开化的年代即提出这样的爱情观也说明了他的对人的本性的解放的推崇,是他的人文情怀的体现,也是其对人的本性和爱情的尊重。
郁达夫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即是其中饱含的深刻的人文关怀。他同情弱者,怜悯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下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被封建礼义所荼毒的人民而悲痛。赞扬美丽的纯洁的热爱劳动的灵魂。郁达夫是一个对祖国怀着满腔热血的人,又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在异国的经历使得他敏感,忧郁,而又满怀着对祖国的悲戚的爱。回国后对于人民生活的现状自然感到异常沉痛。他敏感的心使他能够观察到社会各个黑暗的角落,并以笔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薄奠》中,主人公所结识的车夫朋友即是被黑暗社会压迫致死的典型代表,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更是借主人公之口强烈的控诉了社会压迫劳动人民的行为,也表示了作者深切的悲伤。而在《迟桂花》中,作者给予了劳动少女形象高度赞扬,称赞她为:在知识分子之外还不得不添一种情的成分上去,于书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层人的风韵在里头。
第四个特点即是文章中洋溢着的对自然的热爱。依然要从性格说起,郁达夫是一个浪漫的,热爱美的人。自然的美是最纯粹,最神秘也最宏大的美。郁达夫小说中对于自然景物的清丽迷人的描写,无不透露着他对于大自然无限的憧憬和爱,而对于世间污浊与黑暗的厌恶,也使得自然成了郁达夫心灵的避难所。郁达夫曾在《沉沦》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那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真挚地表现了郁达夫对于自然的依恋与热爱。鲁迅说过,革命诗人撞死在革命的纪念碑上。鲁迅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成了革命的纪念碑。那么郁达夫,如同书中的“他”一样,这个面容忧郁的青年,竟最终死于革命。可以我来看,郁达夫无论如何都不具有所谓“革命气质”的,他的“救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在国家危亡时期的焦虑之总和。他对于文体、行文的创新,积极参与文学革命,组建创造社,这些,也大概是他小说的实验。他是文学的天才,不是革命的猛将(至少我这么认为)。换句话说(其实已经说过),国家的落后、弱小,仅为《沉沦》提供了一个背景,一个不可缺少,却时时刻刻被用作借口的背景。
我们从《沉沦》中探寻的,绝不仅仅是譬如“要自强”、“要自信”一类的空话,我们要发现人性,我们要发现“我们”。《沉沦》虽然有极强的私人性质,但总能让读者找到一个赤裸的自己。鲁迅的《孤独者》里有一句:“使人不耐烦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上,一面哀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这形象地描绘了那个时代《沉沦》读者的形象。尽管这是在讽刺无病呻吟,故作忧悒的人群,但这确实反映了《沉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即使是虚假的伤感,读者们仍是努力地“伪装着”在书中“发现自己”,努力地发现孤独。《沉沦》的孤独是真正的孤独:一方面他苦于不被理解,另一方面又拒绝对外界敞开自我。《沉沦》一书,孤独的质量很高。
读《沉沦》,莫若说是在读部分的自己。时代改变,但人性总是共通。我的题目是《浪漫与救国》,但我们需仔细感受的,不仅是浪漫、是救国,还是那个浪漫多情的,忧愁着国家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悟这部小说的魅力。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摘编仅作学习交流,非商业用途,所有文章都会注明来源,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快速处理或删除,谢谢支持。
(原文章信息:标题:郭进拴|郁达夫小说浅论,作者:郭进拴,来源:奔流文学网,来源地址:http://www.benliuwang.com/wenku/Details/1104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