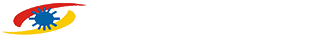余罪为什么这么火?【艺术评论】
- 时间:2016-09-18 10:24
- 来源:文汇报
- 作者:复旦大学 杨俊蕾
网络剧 《余罪》 上线以来,播放点击累计超过60亿次,略等于全球当前人口的总和。是什么吸引了海量的连续观看,让近乎全球人口总量的点击开启各种式样的屏窗?
对于视频终端而言,适逢高价自我兜售的融资敏感期,《余罪》 的旗舰效应构筑起绝佳的形象广告,其中的公关意义远远胜过同行的那个“小时代”系列,哪怕后者的高管如何卖力为“无脑剧”洗地,如何傲娇地一次次宣称那些15到25岁的“少女心”观众赐予他有史以来的最高投资回报,生怕别人把他误会为同样的“无脑族”。
《余罪》 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籍在山西的互联网写手常书欣仿佛从明清之际的评话说书人转世而来,在《余罪》 中再次显影了一个高度民间化的本土世界。这个仿古环境充溢着水浒似的草莽英雄气,很多在青年教育中长久以来充当核心概念的词汇,变成了真实可感的个体艺术经验,带着有体温的真诚情愫,刷新警匪小说的阅读与想象。
常书欣笔下这个名为“余罪”的主人公既贱且痞,故事属于罪案类型,多处大幅煊写暴力,但与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 的少年叙事相比,逊色了一段抒情的诗意;文中常见大段的浪游描述,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 《小癞子》 参照,少了很多艺术化的多彩波澜;而作为最引人入胜的警员探案环节,尽管层层抽丝,步步剥茧,但相较于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显然缺少厚重的百科知识作为扎实底蕴。
然而,也正是这个“一心从众滥竽充数”的青年,通过实打实地刻苦工作成为“脱颖而出的警界先锋”,围绕他的形象又聚拢起很多可供辨识的青年群像。在中国古典传统都已一一被短视而急功近利的投资人翻拍成伪魔兽电影的今天,在电视荧屏上到处充斥着海外版权节目的今天,“余罪”和他的朋友们,这群真实而独特的中国小镇青年,人生故事中不混杂异域文化的摹仿,形象塑造也部分地远离了概念先行的功利主义,恰恰揭示了一个被忽视已久的重要现实:在“小镇青年”这个笼而统之的概念之下,是无数个独特、真实的乡土青春。
这样的青春里,有我的乡土与兄弟
所有关于青春的叙述都带有特别的感染力。海明威对年轻人说“这个世界很美好,值得为之奋斗”,聂鲁达则说“生命如此丰富,而且充满哀伤”。关于青春的感知和描述如果不是为了廉价催情,就往往宿命般的兼具极美的激情,以及热情焚尽后的彻骨离殇。
《余罪》 青春的第一度自由出自土生土长的“老西儿”身份,来自这些青年对于自身乡土的清楚认知,以及不问缘由的依恋和热爱。在当前北上广云集了最大多数青年就业的时代表征下,《余罪》 使人们看到,那些不曾远离故乡的年轻人是如何有意义地度过小镇上的青春。继而,围绕“余罪”的一干青年兄弟,同样的卑微贫穷,又同样的热血义气。他们互相理解彼此身上的毛病、癖好,甚或劣根性。
比如“余罪”促狭,频搞恶作剧,能渔利就绝不放过机会,从不故作清高;“鼠标”严德标好利贪便宜,眼光短浅,一旦能赢个把小钱儿,天大的任务也抛去脑后;至于“技术宅”骆家龙,一方面段位已经高到准电脑极客,另一方面却不谙世情,为了生计竟然吃住网吧,帮着逃课小学生打通关游戏。还有“牲口”张猛,身强体壮没心机,或者说压根没头脑,为人正直,却对社会逻辑一无所知,一旦落难就瞬间返祖原始人状态,拼一把子蛮力,将就着存活下去。
除了这些活灵活现的个性人物作为割头换命的同袍兄弟,“余罪”的青春岁月里还有为数不少的平淡之交,谈不上友情甚或交情,却在默默中不计回报地互助一臂之力。如果这样的行为存有什么动机,也只能理解为同出寒门的心有戚戚。譬如周文涓、董韶军,毫无家世可言,祖辈数代都是农民,来自贫寒乡间,然而他们身上却不乏鲁迅先生所期许的脊梁骨气和韧性战斗精神。原著第1卷第27章,长于市井而无比精明的“余罪”隐隐窥出处长许平秋一心想要招揽自己入警队,他以自己为筹码提出一个要求,要求许处长同时招收“要素质没素质,要相貌没相貌”的周文涓作女警,原因是“她根本没有出路,如果给她个机会的话,她会拼命干好……这次选拔不就是挑能去一线拼命的人?”
事实亦是如此,在羊杂店打工挣学费而不能回家过年的周文涓爆冷进了警队,分在冷僻的法医学,到罪案现场学习采证。董韶军则去了更为冷僻的痕迹检验研究所,听起来高大上的“犯罪痕迹学”在实干中就是提取并分析“人体的排泄物、汗渍、血渍、体液、毛发……”这些平凡且贫穷的年轻人们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在那些不受青睐的冷门岗位上一门心思钻研,最终凭借在一线上积累的专业知识技能协作互补,屡破奇案;同时凭借扎实过硬的个人技术逆袭为单位里须臾不可少离的业务骨干。《余罪》用平缓的笔调写出了小镇青年怎样通过实打实的刻苦工作,将自己发展为有社会价值的职业人,使“小镇青春”具有了自我实现的自由度。
海量点击背后,是十足中国气质的英雄情怀
“余罪”脚下有深植大地的根,一旦获得警校放假就忙不迭赶回单亲的父亲家里,帮忙打理水果摊小生意,简直复刻了孔夫子名言,“吾少贱,故多能鄙事”。“余罪”身边总有兄弟围绕,从牢狱卧底到破获毒品大案,从村庄最基层的乡警到城市最基层的反扒大队,每一桩奇功荣誉都离不开兄弟相帮,以及警匪题材中特别重视的集体合作精神。这是原著中着意挥洒的部分,然而在网剧 《余罪》,尤其是第二季的改编中,却恰恰在这点上和原作小说分道扬镳。
作者常书欣发微博:投资方买断版权,却宁可另编一个新故事,和原著完全不同,毁了余罪IP。力挺原作的忠实读者们也纷纷登上豆瓣给第二季打出低分,于是一边是飓风般增长的数十亿点击量,另一边却是疾速暴跌到勉强过7分的成绩。网剧方的托辞是原作涉及太多黑色犯罪心理和残酷罪行描写,再加上和现实太近距离的话题又敏感又尖锐,故而必须向年轻人倾斜,变成青春偶像的样式。网络小说和网络剧原本共同依托互联网存在,在“余罪IP”上竟然出现“相煎何太急”的荒诞场面,造成网剧远逊于网文的主要原因,就是貌似青春剧的改编流失了小镇青春独有的二度自由。
小说 《余罪》 中的青春是多声部合唱,既有发自个体自由的民谣小曲《兄弟》,也有代表集体感召力量的《警察之歌》。网剧倾向前者,出于畏难,放弃了探索人物心理动机的集体精神线索,恰恰错过了最令中国青年们激动感怀的“吾土吾民”情结。《余罪》 原著写到“偷牛案”,假借村民丢牛的案件串连起三晋大地上的大量地名,朔州、吕梁、阳高、应县,甚至是偏远到省界的小村庄,观音庄、后沟、涧河……这些地名在讨论案情时被浑不吝的年轻人们一一举例,包涵着心系吾土的族群归属。犹如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 《我的团长我的团》,龙文章在疯癫庭审中足足说了30分钟的南北地名,从南京、上海直到武昌、汉口、修水、宜昌,最后是怒江、保山、腾越和禅达。凡对中国抗战历史有知的观众都禁不住泪崩,佯狂的疯话后是举国痛心的战争失利顺序,是1938年严冬之后次第沦陷的国之厚土。
乡间偷牛案激发了人之为人的“不忍之情”,“这事怎么着也让人觉得心里堵得慌”。内心本能中的怜悯促使青年们超越了囿于自我欢愉的自利主义和快乐原则,升华为超道德的社会价值询唤回应,将自身的主体能力与心智智慧“主动而自由地”置入“集体对我的需要”,通过扩大行为的利他性质,推升个体价值的境界。小镇青春中的二度自由至此表现出超越物欲、超越拜金的精神况味,就像“余罪”的带教师傅慢悠悠说体会,“清洁的精神总是蛰伏在每个人心里不知名的地方,在危难的时候,在命悬一发的时候,这种精神就会出现,会主导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让他干出不可思议的事,于是,这个世界就有了英雄。”
难道不正是这个十足中国气质的英雄梦境吸引了数十亿的点击? 有为的青年们终将体验有温度的热血人生,不虚掷青春,亦不让渡自由。这个小镇青年从赋形伊始的“贱人余”一步步成长为“以血为证”的勇士,在无形中重合了斯皮尔伯格最为尊崇的“内心故事”:英雄不是文学中的构想,他们是所有历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