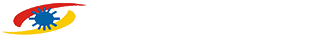黑狗往事
- 时间:2024-08-19 08:45
- 来源:会员中心
- 作者:黄三儿
黑狗三部曲包括《黑狗往事》、《狗娃》、《河葬》。《黑狗往事》描写的是生活在农村或乡下的狗,或者叫有农民身份的狗;《狗娃》描写的是原来归属于不同主人的狗,或者叫有宠物身份的狗,后来由于生活的变故,而变成了流浪狗或自由的狗;《河葬》描写的是生活在水文站或相对在城市的狗,或者叫有市民身份的狗。
第一部 黑狗往事
黑狗往事
这是一只生活在乡下的黑狗,当他面对野狼侵害主人的牲畜的时候,他毫不畏惧,勇敢地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与野狼进行殊死搏斗,并最后战胜野狼;当他囿于人类之间相互明争暗斗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无奈且孤独无助,被迫成为人类的牺牲品;当他年老体衰、苟延残喘的时候,最终却落得一个被出卖的下场。
——作者题记
一、 野狼
1.野狼在嚎叫
约莫四更时分,桂娘家囡囡的啼哭声,惊醒了张三爷。张三爷开始醒来时,只是睁开了双眼,眯眯瞪瞪地躺在充满黑暗的床上。自从这个囡囡出生到现在,突然的啼哭对张三爷来说虽然已经习惯了,但总是有点心烦。张三爷听了一阵后,见没有要停的意思,骂了一句死丫头,便披衣坐了起来。张三爷顺手把枕头竖起来,靠在背后。张三爷斜过身子,伸手在灶台上摸索了几下,就把长烟袋叼在了嘴上,抖着手用火柴点着了烟锅。火柴在“嚓”的一声中瞬时点亮了房间,一股旱烟味呛醒了睡在张三爷身边的老伴马姑,老伴嘟哝了一句“又吓鬼呀!”翻了个身,脸朝里又睡着了。
张三爷嘴上抽着旱烟,耳朵里听着令人心烦的囡囡的哭声,心里憋着一股说不出的闷火。突然间张三爷愣住了,在囡囡的哭声中还夹杂着黑狗凶猛的叫声。张三爷仔细辨别着狗叫的方向,当他就要断定其狗叫的方向时,又突然被囡囡的哭声所淹没。张三爷起身走到窗户跟前,把耳朵紧紧贴在窗棂上,从凶猛的狗叫声中清晰地判断出,老黑狗正在牛王山下与野狼搏斗。张三爷确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误时,他懊悔昨晚为什么没有把那块已经发臭的猪皮都让黑狗吃了。张三爷想起这些,嘴里不住地说:“老黑狗呀,老黑狗。”
在黎明到来之时,桂娘家囡囡的哭声渐渐停歇了,好像哭累了,也好像又熟睡了。张三爷看见窗户已经放亮,索性提上裤子起床。实际上,这时的天才麻麻亮,房子和房子之间还掩映在黑影之中。当张三爷走到院子中间的时候,听到东屋的外间传出一阵急促的“沙啦啦”的声响,他知道这是桂娘正在排泄,她排泄的声音从来不避讳,而且拉完之后,并不影响她爬进被窝再睡一个黎明前的回笼觉。
打开大门的时候,张三爷看见老黑狗卧在门槛前,老黑狗知道这么早开街门的全村只有张三爷。听见门响,老黑狗站起来,好像很吃力,但张三爷并没有注意到,再说老黑狗在与各类野兽搏斗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受过伤。张三爷跨过门槛,老黑狗亲热地用头在张三爷的小腿上噌了噌,算是与张三爷打过了招呼。张三爷弯腰用宽大的手抚摸着老黑狗,老黑狗知趣地摇动着尾巴。张三爷感觉到老黑狗的毛皮上非常湿润,摸过的手就象水洗了一般。张三爷知道老黑狗与野狼的搏斗肯定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老黑狗你出这么大的力气又是为了谁家呢?
张三爷站起来,把鞋子提上,顺着街道向西走去。走到街的西口往南拐,张三爷看见那一排猪圈的旁边站着一个人。他快步走过去,见是张老栓的胖女人,就没好气地问道:“黑灯瞎火的你在这儿干啥?”
听见是张三爷的声音,胖丫慌忙说:“野狼咬了我家的猪,那畜牲也真够狠的,一嘴咬在了脖子上。”
张三爷听了胖丫的话,觉得问题很严重,又问:“咬死了?”
“没有,还流着血呢,就是止不住。”这时,张老栓在猪圈里答道。
张三爷瞅了瞅猪圈,对张老栓的女人说:“还在那儿傻站着干啥,快回去撮点锅灰,抹在狼咬的牙口上。”
“是、是、是。”胖丫答应着,但并没有挪动脚,直到张老栓在猪圈里举起一只血手向他挥舞,她才悻悻地扭着肥硕的屁股回家。张三爷疑惑地问张老栓:“你咋就知道是你家的猪被狼咬了?”
“我听见了,昨晚我睡在西厢房,是二闺女来了。开始,我睡得死死的,后来听见那猪沉闷的叫声,感觉事情不妙,我就扒在窗户上看,……”
张三爷打断张老栓的话,问道:“还是那头狼?”
“是的,还是那头狼。不过这次是两只,除了那头老狼,还有一条半大的小狼。这两头狼一前一后围攻那猪,最后是那头小狼扑过来一嘴咬在了猪脖子上。”
“端来了,端来了。”胖丫端着一屉锅灰,走到猪圈旁,递给张老栓。张老栓抓起锅灰一把一把拍在仍汨汨流血的猪脖子上,拍上的锅灰很快被流出的血染湿了,于是张老栓又继续往上贴锅灰,张老栓象拍锅贴一样渐渐糊住了猪脖子的伤口。那畜牲流了许多血,身体显得十分虚弱,便老老实实地趴在草窝里,喘着粗气。
张老栓站起来,伸了伸蹲麻的双腿,拍了拍身上沾的猪草,跳出猪圈,看见了张三爷身边的老黑狗,激动地说:“三爷呵,可是多亏了你家的黑狗,若不是黑狗及时赶来,我家那畜牲这会儿早就被剥皮下锅了。”
猪圈的东边就是张老栓的房子,中间隔着一条斜街。张老栓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他为了观察猪圈特意在西墙上开了一个窗户。
天已经大亮了,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整个村庄。张三爷想去河边转转,扭头绕过张老栓家的猪圈。突然被张老栓从背后喊住,“三爷,地上有血,黑狗的腿好像也瘸了。”张三爷听见喊声怔在那里,张老栓走到张三爷跟前,指着路上的血迹说:“三爷,你看,两溜血迹。呵,黑狗腿上还在滴血。”
张老栓摸了一下黑狗的后腿,证实确实在流血。张老栓抬起头问张三爷:“要不,也用锅灰贴一下。”张三爷摆了摆手说:“不用了,我回去给它包扎吧。”
张三爷掉转头回家,看到西街的青石路上也粘着黑狗的血脚印,象是梅花缺了两个花瓣的三趾脚印。这是黑狗的脚印,那是它与野狼搏斗结束后回家留下的。张三爷看着那些血迹斑斑的脚印,生气地问身后的张老栓:“老栓,你没有出门,你咋知道是你家的猪被野狼咬了?”张老栓有点委屈地说:“那阵儿,我正要出门,黑狗来了。黑狗把那两只野狼撵出猪圈,就在猪圈外摆开了搏斗的架式。我看见黑狗越战越勇,一个箭步翻身就咬住了那只小狼的后腿,并把它掀翻在地,迅疾换口咬住它的脖子。这时,黑狗被窜到他身后的那只老狼咬住了后腿。黑狗松开那只小狼,掉头扑向老狼。老狼见黑狗松开了小狼,只听老狼“嗥”的一声,见势带着小狼脱离了战场,一溜烟向河边逃去。黑狗肯定是忍着剧痛,在后边紧追不舍。
“你看见狼跑了,才出来看你家的猪。”张三爷嘲讽道。
张老栓哑口无言,显出一脸的无奈,“唉”的一声算是回答。
张三爷回头看看忠实的黑狗,好像醒悟过来,问张老栓:“老栓,四更天那会儿,我象是听见了黑狗的叫声,听其声音好象是从牛王山下传过来的。”
听张三爷这么一说,张老栓又提起了话头。“黑狗和野狼在这儿搏斗的时候,你可能没听见。你听到的是黑狗把野狼追过河对岸,在牛王山下与狼的第二次搏斗。”
张三爷好像突然明白了,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然后对张老栓说:“张老栓呀,张老栓,你真是个鬼精灵。”
当张三爷和张老栓从影壁走出来的时候,桂娘恰好端着尿盆从东屋出来。桂娘头发零乱,上衣的扣子也没系上几个,从近乎敞开的胸口可以清楚地看见两只饱满的乳房沉甸甸地快要撑破贴身的小背心。张三爷咳嗽了一声,近似于对桂娘的指责。桂娘急忙用手往一块儿拢了拢领口,低下头三步并作两步拐进了茅房。桂娘显然觉得不好意思,她没有料到张三爷今天怎么会这么早就从河边转悠回来,而且屁股后面还跟着张老拴。桂娘蹲在茅房里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从茅房下面吹来的冷风使她暴露的部位有点发凉,才终止了恼心的思维。
桂娘从茅房出来,便走边抿鬓角的头发,抬头看见张三爷和张老栓不知道围着黑狗正忙活什么,只听见张三爷说:“布条不要缠得太紧了,以免捂得太热,伤口发炎化脓。”
“知道了。”张老栓说:“黑狗真是一条好狗,他通人性。三爷,你看他,受了伤一点也没有表现出疼痛的样子。”
张三爷没好气地说:“狼又没有咬在你身上,你咋知道个疼?”
桂娘走回东屋,关上门嘟囔道:“不就一条狗吗,又不是你儿子。保不准那畜生又去哪儿骚母狗了,叫人家主人打伤了腿。”
张三爷和张老栓给老黑狗包扎好,老伴从里屋给黑狗端来了一盆热气腾腾的食物,放在黑狗的面前。随后,又拿起一块干净的布为黑狗拭去皮毛上的汗水。
当太阳驱散了天空弥漫的雾气之后,张三爷看着黑狗安详地闭上眼睛卧在香台下面,便回到小西屋去翻找他那久违的猎枪。张三爷提着猎枪坐在堂屋的石阶上,吆喝老伴再取一块干净的布子来,并顺便把那罐猪油提过来。张三爷先把枪身擦干净,然后拔出通条,仔细地把通条上的锈斑打磨掉,再绑上布条伸进枪膛上下来回地擦拭。通完枪膛,张三爷用嘴对着枪口吹了两口气,当他听到很清亮的“噗、噗”声后满意地笑了。除了枪膛,张三爷又格外认真地试着扣了几次扳机,感觉到顶针能够在瞬间准确无误地击在子弹的簧上才真正放下心来。
2.马姑对黑夜的恐惧
老伴马姑看到张三爷又在擦拭他那杆破枪,在她的内心油然生出一种无名的怒火。她之所以说张三爷那杆猎枪是什么破枪,不仅指那杆猎枪已经年代久远,而且是指三年前张三爷那次鬼使神差为了追踪一只狐狸迷失在祖坟而险遭厄运,以年龄不饶人的借口就不再怎么摸这杆枪了。假如是年轻的时候,只要张三爷闲暇下来,他都会扛上猎枪满山去搜寻那些豺狼野兽,以至于附近的山里几乎绝了野兽的踪迹。
随着张三爷岁数的增长,她虽然感到张三爷有些衰老但身上的家什并没有因此而颓废,反而更加雄壮有力,有时她实在忍受不了。
看到这杆猎枪,马姑至今还心有余悸,因为当年就是这杆猎枪逼着她离开了繁华的都市,来到了这个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的关虎屯。马姑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她还在熟睡的时候,突然被一阵乱嘈嘈的撞门声惊醒了,当她睁开眼睛看见一群手拿利刃的家伙站在屋子的中央,惊恐万状地搂住丈夫的脖子,而丈夫却显得异常地镇静,拍拍她光滑的脊背告诉她:“这些家伙是冲着你来的。”
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端着猎枪一直走到床前,用枪指着她丈夫的脑袋,一本正经地说:“掌柜的,今天如果你还不兑现的话,我这一枪下去,你的脑袋可就变成了漏瓢。”
“兑现,兑现,现在你就把她带走。”丈夫哆嗦着掰开马姑的双手,无力地说:“你跟着他们走吧。”后来马姑才知道,那端枪的家伙就是张三爷,她是作为筹码在一场赌博中被丈夫输掉的。那天晚上,张三爷端着枪逼着她穿上衣服,然后又用枪顶在她的屁股上直到离开她的家。马姑现在想起那夜的情景,总会下意识地摸一摸臀部, 因为稍有反抗,她那白嫩的屁股可能就会剩下一半。
马姑跟着张三爷来到乡下,就变成了张三爷的老婆。有天晚上当张三爷办完事后,笑嘻嘻地告诉她,实际上他早就看上了她。那是在他和她的丈夫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当他看见她丈夫身边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时,顿时就被她的美貌迷住了,所以就有了那次精心设计的赌局,张三爷的目的达到了。在马姑明白女人的命运就是在男人之间跳来跳去之后,也就死心塌地跟张三爷过起了日子。
在寂静的乡下,马姑和张三爷过着平淡的日子。张三爷长时间频繁地耕耘,并没有得到任何收获,便开始将一股子邪火发泄到马姑的身上。马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就不会生养,如果会的话,为什么跟第一个丈夫好多年竟然没有怀上一个?不过也怨不得自己,谁让他有那么多老婆。可是,张三爷就她一个女人,也没有见他去打过野食,难道自己真成了一个不会下蛋的鸡吗?
那天,张三爷打猎回来得很晚,回到家满嘴还喷着酒气。张三爷把猎枪靠在床头,屁股重重地压在床上,只是不停地吧嗒着旱烟。
马姑战战兢兢地站在张三爷跟前问:“你还吃饭不?”
“不吃了,吃你。”张三爷劈头盖脑地吼道。
张三爷斜了一眼马姑,抬起脚在鞋底上磕掉烟灰,闷声闷气地说:“把衣服都脱了。”
“天还早着呢,月亮刚上来。”马姑小声说。
“天早不早跟我有啥关系?我要给你治病。”
马姑顺从地脱光衣服,平躺在床上。这时,一缕清冷的月光斜照在宽大的床上,月光如水洒在马姑平坦的腹部。马姑躺在床上,无奈地闭上眼睛,等待张三爷火山一样的爆发。可是,等了半天并不见张三爷的动静。马姑睁开眼睛,看见张三爷又点上了旱烟,烟锅上冒出的火星在黑暗的屋子里就象鬼的眼睛。张三爷狠狠地抽了几口,猛然间对准马姑的肚脐眼扣了下去。
马姑被这突如其来的火烫疼得杀猪般嚎叫起来,“你这挨千刀的,要杀我,你来个快点儿的。”
张三爷不慌不忙地说:“我不会杀你的,我这是在给你治病。”说完,张三爷往烟锅上装好了烟叶,重新将马姑肚脐眼上还发着红光的火吸在了烟锅上。如此反复,顺着肚脐一溜扣到了毛茸茸的地方。屋子里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旱烟和毛发烧焦的糊味,马姑的叫骂声渐渐被断续的抽泣替代了。
时间仿佛在张三爷的恶作剧中凝固了。张三爷机械地重复着相似的动作,在他犹豫了一阵后,点燃了最后一袋烟,他小心翼翼地将烟袋一直伸进马姑的身体里面,马姑麻木的神经再次在强烈的刺激下条件反射地嚎叫起来。张三爷使劲吸着烟嘴,不断地喷吐出烟圈,直到他吐出的废气中再也没有了烟味,才将烟锅抽了出来。当张三爷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又开始了艰难地开垦。以致马姑害怕黑夜的来临,只要太阳一落山,马姑的身心就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紧紧地攫住。当这种残酷的刑罚却被张三爷叫做治病的方式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生活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与平淡。张三爷仍然早出晚归醉心于跟野兽类似于捉迷藏的搏斗。
村边的小溪开始解冻了,从河里袅袅升起的水汽表明天气逐渐变暖。春天来了,马姑的肚子也变大了。每当张三爷晚上用那双握惯了枪的手摸着马姑光滑的肚皮,便得意地对马姑说:“多亏了那烟袋,是它把那邪鬼给驱跑了。”
马姑想起那些生不如死的夜晚,心情就会痛苦不堪。然而,在接生婆给她接生的时候,突然看见她肚皮上那一溜青灰色的烟圈,却把眼睛瞪得圆圆的,表现出十分惊奇的样子,随后就是赞不绝口。她看到马姑毛丛中的那个明亮的烟圈,越发肯定马姑是仙女下凡。接生婆后来逢人便说,马姑根本不是凡人,而是天上的仙女投胎转世。有时候还绘神绘色好像很在行,说:“那是媚心,仙女的标志,只有下凡的仙女才有。”因为她就没有,而且她所见过的女人也没有。
因为只有她,才有机会看见其他女人的隐秘,加上马姑来到关虎屯本就来历不明,所以人们都相信接生婆说的话绝对是真的。通过接生婆的广泛宣传,方圆几十里都知道张三爷的女人是仙女,根本不是地上人间的俗女人。
马姑第一胎生下的是个男孩,张三爷取名叫张福生。三年后又生下一个男孩,张三爷高兴地取名叫张广生。张三爷原以为他的播种能够人丁兴旺,却不料当马姑生下张广生之后,那源远流长的生命之源就根尽枯竭了,但马姑的身体并没有向坏的方向发展,依然妩媚无比,标致宜人。
3.张三爷寻狼
平常,黑狗比较温驯,讨人喜欢,囡囡和黑狗经常在院子里转圈圈玩耍,每当囡囡把手里举着的诱食扔下来被黑狗腾空接住,囡囡就会肆无忌惮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桂娘回到屋里,越发不明白,何故一夜之间黑狗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而囡囡的一夜啼哭却无人过问。何况男人一走几个月的不归,孤寂难熬的长夜更使她心情烦躁透顶。当她看见张三爷坐在门口擦拭那杆猎枪的时候,她神经质地嗅出了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味而不是火药味,她弄不清楚张三爷今天那根神经出了问题又把那杆枪拿了出来,莫不是又要用枪给她抢回一个婆婆。
黑狗勇斗野狼的佳话传遍了河沿一带,对黑狗比较了解的人更是对他赞赏不已。同时,野狼的出现警告人们最好在夜里不要外出,否则的话,就有可能遭遇张老栓家的猪同样的命运,届时黑狗会不会再次出现谁也不敢打保票。张三爷背上猎枪,嘱咐了老伴几句话,就出发了。
张三爷顺着路上的血迹一直追到牛王山下,血迹在这儿拐下了大路,沿着老桥沟进了南山。南山的腹地是一片茂密的老林子,张三爷许久没有进山了,对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木已经有些陌生。假如时光倒退十年,即使野兽们放个屁,他也会分辨出那个是公的那个是母的,从而追踪到他们的藏身之处。张三爷凭着多年与野兽打交道的经验,他认为那两只野狼是从外地偶然流窜过来的,很可能是被其他猎人追得山穷水尽,实在饿得没有办法才跳进张老栓家的猪圈咬了那笨伙。尽管老早以前也有野兽袭击牲畜的事件发生,但那会儿是兽多肉少,其实野兽内部不是也自相残杀嘛。有时,张三爷上山的时候就碰到过被咬死的野猪、野狼、野獾,剩下半拉子撩在野地里。
夕阳如快要熄灭的炉膛火,染红了西岭的半边天,透过树木的枝枝桠桠射进来的阳光,使张三爷感到南山的这片林子有点光怪陆离,突然一种孤独的感觉袭过张三爷的心头。隐没在老林子里的几个山头包括悬崖下的几个岩洞,都被张三爷一个不漏地搜索过了,除了几堆野猪的干粪,竟然没有发现野狼出没的痕迹。随后,张三爷特意把以前掏过獾仔的土洞用黄蒿薰了一通也无济于事。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张三爷把随身携带的几只套子沿各个岔口下好,把逮住野狼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几只套子上。当他来收套子的时候,期望能看到这两只野狼在他下的套子里作垂死挣扎。张三爷看惯了野兽们在套子里苦苦挣扎的样子,每当他看到这种情景,就抑制不住兴奋,一股快感便会传遍全身。 张三爷布置好套子又重新检查了一遍,直到满意才将双手使劲在裤子上搓了两把。
张三爷在南山上转悠了一天,始终没有发现野狼的踪迹。他走在大街上,没有碰到一个人,也许是野狼的缘故,家家户户都早早地关上了大门。张三爷迈着沉重的脚步跨进门槛,也转身紧紧地关上了大门。他走到香台前,摸了摸黑狗的后腿,见布条上再没有渗出鲜血,便放心地回屋去了。
二、诱惑
1.飘动的绿眼睛
张三爷没有寻到野狼的踪迹,随便吃了点饭便躺下睡着了。
马姑自从为张三爷生下两个儿子之后,逐渐对黑夜的恐惧淡漠了。可是,今天看见张三爷出去了一整天,最后竟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感到特别失望,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涌上她的心头。马姑躺在张三爷的身边,端详着他熟睡的样子自己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没有见过野狼,自然不知道野狼的凶残。
冥冥之中,马姑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家。那天晚饭后,马姑信步来到了后花园。花园靠南一隅有一排低矮的平房,里面住着仆人和丫环。当马姑走到回廊尽头的时候,正好听见刘嫂正在给她的小儿子讲故事。刘嫂说,从前有个贪玩的孩子,天黑了还不回家。有天晚上,天空中到处飞舞着闪着绿光的萤火虫,孩子们戏闹着追逐着上下翻飞的萤火虫,相互分享着逮住萤火虫的乐趣,天真无邪的笑声回荡在夏日晴朗的夜空。这时,一双迅疾移动的绿光出现在那个不听话的孩子面前,他忘乎所以,以为是两只硕大无比的萤火虫。他笑着向那两只会移动的绿光跑去,他脱离了小伙伴远离了母亲。当他就要扑上去的时候,人们听到了他的惨叫,他是在绝望中喊着妈妈被那双会飘的绿眼睛叼走了。那两只绿眼睛长在狼身上,是狼把那个不听话的孩子叼走了。
那双飘动的绿眼睛重新闪现在马姑的脑海,她好像就是那个不听话的孩子,想喊却喊不出声来,她四肢徒劳地挣扎着。
当马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被野狼两只发绿的眼睛惊醒,本能地死死抱住张三爷的脖子。张三爷在马姑的重压下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并扯开嗓子喘着粗气歇斯底里地高喊:“我的枪,快、快给我的枪,打死它,打死它,你这个狗娘养的。”
“呃,枪,我给你拿枪、拿枪。”马姑赤脚跳到地上,一把搂过床头的猎枪递到张三爷的手上。当张三爷拎起冰冷的猎枪,才从噩梦的深渊中清醒过来。马姑看着张三爷紧紧地握着猎枪怔怔地坐在那里,便对他呼喊:“你为啥还不开枪?快开枪呀。”马姑右手随便乱指着充满黑暗的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你快看,有双飘动的绿眼睛,在屋子里到处飘荡。”
张三爷看着马姑害怕的样子:“打啥呀?刚才我做了一个噩梦。”
马姑关切地问:“梦见了什么?”
“我梦见了那只钻进祖坟的狐狸,这次我好像又被那畜牲骗了。”
“啊,刚才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两只发绿的眼睛在屋子里游荡。”
“行了,睡吧,刚才咱们俩都做了一个噩梦。”
2.黑狗得到了爱
在养伤期间,黑狗除了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前来观望,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东街的黄狗以及在三邻五村的狗伙伴对他的热情探望。东街的黄狗是一条年轻的母狗,她对黑狗这次与狼搏斗的勇敢精神大加赞赏,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怀,她把主人施舍的包括在野外捕获的和一切能够搜罗到的营养食品统统送给了黑狗。黑狗不负众望,身体迅速复原。但是,被野狼咬伤的那条腿虽经张三爷精心调治,最终还是留下了残疾,走起路来稍微有点瘸,也就是说,黑狗成了瘸腿的狗。不过,一旦奔跑起来,任谁也丝毫看不出黑狗的腿有残疾。
黑狗和黄狗的感情日渐升温,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他们俩相好,张三爷始终没有发现,倒是桂娘连续几个晚上跑肚子拉稀偶然撞上了几次,尽管她对狗们之间的龌龊不甚感兴趣,但相对于孤寂的自己倒还是着实兴奋,乃至躺在床上把手放在那个敏感的部位,竟然感觉到了一种异常的发自内心的冲动。
关虎屯的十字街原先并不存在,只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原来的基础上向东南和西南方向逐步发展才形成了现在的格局。黄昏时分,人们在十字街头无聊地谈东论西,野狼的出没以及黑狗的勇敢业已不再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低级趣味的男女情事和东家长西家短的婆媳关系又变成了他们主要的谈论对象。
黑狗安静地卧在张三爷的脚面上,半睁半闭地听着这群人的东拉西扯。这时,黄狗悠闲自在地从东向西走了过来,旁若无人地走到黑狗的跟前,先用舌头上下左右舔了舔黑狗的鼻翼,尔后又舔过黑狗的眼睑和耳根。黑狗似乎明白了黄狗的意思,便站了起来。他们相互吻舔着对方,耳鬓斯磨。黄狗对黑狗的亲昵逐渐引起了黑狗的兴奋,但黑狗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开始对自己感到失望并有些气馁,莫非自己真的老了?老的再也不中用了吗?不,黑狗心里不服气。
黑狗把他的想法告诉黄狗,黄狗的情绪经过调整很快缓和并逐渐趋于平稳。他们忘乎所以,尽情地享受这种微妙的情感带来的片刻欢娱;他们无拘无束,在人们的面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他们不想半途而废,为了那些伪君子放弃这种自然情感的流露和表达。黑狗和黄狗的激情终于招来了好事者的干涉,于是土块、石块交替落在他们的背上,甚至还有一些正经女人的肮脏的唾液被蔑视地吐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于是,黄狗和黑狗开始逃离了。但他们的身后还有几个娃娃和年轻人跟在后面穷追不舍,他们只是猎奇还是别有企图不得而知。黄狗和黑狗不停地奔跑,最后跑到河边躲在一个不过水的桥洞下面,等待黑狗完成最后的温存。
3.酷暑下的狂躁
翌日清晨,张元睁着惺忪的眼睛走出了街门,当他就要拐上正街的时候,抬头看见桂娘端着什么东西进了茅房。百无聊赖的张元也忽然觉得应该释放一下,便不由自主地走进茅房。乡下的茅房没有太多的讲究,一般家户都是男女公用,而张三爷家的却与众不同,之间一墙之隔分开男女,但下面的茅坑却是相互连通的。张元面带慍情地站在那里,听着隔墙那边不断传来的瑟瑟声,一会儿便有一股水流喷射而出,水流呈弧形急促地拋射在坑壁上,然后哗啦啦顺着坑壁流向坑底。张元盯着那股弧形的水流目瞪口呆,他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注意过女人放出的水流也会呈现弧形,他感到实在太意外了,以至于他痴痴地走出来时都忘记了自己是否尿过。
桂娘大大咧咧地回家,张元目不转睛地盯着桂娘的臀部,随着脚步的移动,桂娘那丰满的臀部一左一右交替地上下耸动,他觉得桂娘那个地方真是太迷人了。桂娘走到门口下意识地向后扭头,看见张元跟在自己身后冲他莞尔一笑。张元见桂娘停住了脚步,还以为桂娘察觉了他在茅房窥视她的秘密,便站在原地等桂娘对他兴师问罪,后见桂娘对她只是甜甜地抿嘴一笑,也就勉强对桂娘笑了笑。
整整一个上午,张元无精打采,象丢了魂似的,东西街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不知道干什么好。临近中午,太阳直射到地面上,使人有种酷热难耐的感觉。柳树上的知了越是炎热越不知疲倦地阗躁。
“知了,知了,你烦死人了。”张元随声骂道,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家门口。他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后院爷爷的家。
张福生是张元的父亲,在他成家立业之后,张三爷便将四合院里的南房分给了他,原先合走一个大门,后不知何故,张三爷在南房前又给张福生圈了一个院墙,这样张福生就成了独门独院。张福生成年后,学了一手好木工活,而且还无师自通会画墙围。张三爷给他成家后,他基本上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养家活口,一年四季除了农忙回家收割庄稼,就是在外村走街串巷地为人家做家具干活挣钱。张元是他的独生子,他从来也没有怨言,只是想等儿子长大了,把他的手艺传给儿子。
张三爷让张福生另立门户之后,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张元一般不会进这个大门。今天,张元觉得自己有点蹊跷,但既然来了,就进去看看。张元走过影壁,一眼看见桂娘正光着上身坐在屋门口冲洗。桂娘起先一愣,迅速用两手护在胸前,问道:“元,你有啥事?”张元随口应道:“找我爷爷。”
“你爷爷、奶奶不在。”
“哦,爷爷不在。”
张元边说边走,一直走到堂屋门前,转身坐在了台阶上。
桂娘见张元不是找她,便继续擦洗。张元坐在那里看着桂娘用毛巾擦洗雪白的胸脯,两只丰满的乳房被桂娘拨拉得上下跳动,就象两只活泼的小白兔。桂娘洗完,使劲拧了两把毛巾,随手端起脸盆将水洒在了院子里,然后转身回屋。
张元的兴致仍然沉醉在桂娘那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之间,突然听见“哗”的泼水声,使得他的思绪猛地一震。他站起来,竟不由自主地进了东屋。张元很少进桂娘家的里屋,最初的摆设只是停留在儿时的记忆。
进得门来,张元四顾环视了一下房间的全貌,他看到最主要的变化是张广生和桂娘原先睡觉用的大炕变成了一只大木床。这时桂娘站在窗前更换衣服,一股压箱的樟脑味扑鼻而来。张元陶醉在这樟脑味和桂娘身上挥发的香皂味之中,她走到桂娘的身后,伸出双手拦腰把两只幼稚的小手捂在了桂娘前胸最柔软的地方。桂娘被张元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扭过身来厉声喊道:“元,你要干啥?”张元喘着气说:“我想吃你的奶。”
桂娘拿开张元的手,平静地说:“傻蛋么,吃你娘的那门子奶呀。再说,你都这么大了,一口还不给我咬掉啊。”
张元着急地说:“不会,不会。昨天在十字街口,你不是也看见黑狗和黄狗在那儿咬了嘛。狗都咬不掉,何况我呢。”
张元嘴上说着,两只手却没有闲着。尽管张元才十五岁,可他已经长成一个男人,桂娘在张元的揉搓下,干渴的情感突然得到一丝慰藉。张元摸着桂娘这完全不同于自己的柔软的肉体,昨天十字街头,黄狗和黑狗交媾的那精彩的一幕重又闪现在他的脑海。张元让桂娘弯腰扶在床上,然后像黑狗一样爬在了桂娘身上。桂娘雪白的肉乎乎的臀部对张元极具诱惑力,他看见桂娘的两股之间确实有一条肉缝,正如那些老鳏们说的一样,两腿之间夹着一条肉缝的就是女人。张元的那些动作完全来自于对黑狗的模仿,昨天追着黑狗和黄狗到河边的那群年轻人里就有张元,他目睹了黑狗和黄狗交媾的全过程,以致于梦醒之后,对黑狗和黄狗亲昵行为仍然记忆犹新。张元的幻觉与动作并不同步,当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他的思想继续在幻觉的世界里游荡。
事后,桂娘心乱如麻理不出头绪,婶侄乱伦实属大逆不道,尤其当张元快要进行完时,弄得她身上一摊糊涂。当她迷醉的心灵冷静下来,油然一种被张元强奸的感觉。张元什么时候走的,她不知道。桂娘穿好衣服,颓然坐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